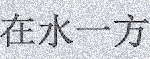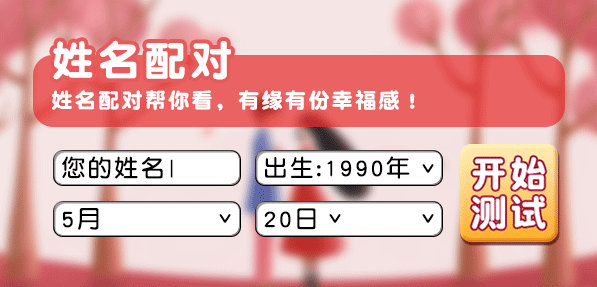大过卦看生死(八字大过伊川)
全文列表一览
1.谁能告知我太极八卦图的解说2.《易经》之游魂卦与归魂卦3.六爻断生死秘传口诀详细解读,八字断生死解析4.卜卦是咸卦 ,变卦是大过卦,请问怎么解?5.《朱子语类》卷三十七 论语十九6.怎样正确对待易经占卜术数
谁能告知我太极八卦图的解说
太极八卦其实就是阐明宇宙从无极而太极,以至万物化生的过程。里边 的太极即为天地未开、混沌未分阴阳之前的状态。两仪即为太极的阴、阳二仪。《系辞》又说:“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其意指浩瀚宇宙间的一切事物和现象都蕴含着阴和阳,以及表与里的两面。而它们之间却既互相对立斗争又相互资生依存的关系,这其实就是物质世界的一般律,是众多事物的纲领和由来,也是事物产生与毁灭的根由所在。
《易经》之游魂卦与归魂卦
六十四卦中,第三5晋卦、第二8大过卦、第三6明夷卦、第六1中孚卦、第五需卦、第二7颐卦、第六讼卦、第六2小过卦共八个卦,叫做游魂卦。
游魂卦的特征着重是变。游的本意就是来往、不固定。魂是飘忽不定。所以游魂卦“变”是主象。游魂卦是将八纯卦1.2.3.5爻,阳变阴、阴变阳而成的。例如乾卦,将第5爻阳变阴,内卦乾变成坤,第4爻、六爻不变成晋卦。将离卦第5爻阴变阳,内卦离卦变成坎卦,四、六爻不变,成讼卦,以此类推,反之回推到八纯。
游魂卦,是事物在本来的纯卦状态下,经经过一步一步自下而上,发展变化了五步之后,从量变即将发生到质变,仅仅保存了本卦的上爻不变的情形下,处于到底下一步怎样变的时刻,接着出现的一个境界和状态。例如乾宫卦已经变了五步,已经到了剥卦状态,到了硕果仅存的时刻,是彻底剥除这个硕果走向象征死亡的坤卦呢,还是逐渐恢复原来的乾宫卦里的阳气呢?这时候,假如顺其自然,就可能发生伏羲卦序中出现的现象,剥卦变化为坤卦。假如生命事物在此关头,能够发挥生命事物的生命力和生命智慧,能够意识到回归本宫卦、恢复本宫卦的重要程度,能够利用这最后的能量和形势,能够将五世卦中的四爻变回本宫卦的阴阳属性,剥卦就变化成了晋卦。避开了死亡,却进入了一个游魂卦境界,可谓死里逃生,还有一线生机。
游魂卦是一个在死亡威胁面前,所作出的英明决策和断然行动,是一个求生存求发展的卦。固然说也是一个艰难的卦,是一个如一丝游魂随处漂荡的卦,是一个心无所安、身无所定的卦,但毕竟一息尚存。只要有这一口气,魂魄会归来。就乾宫的剥、晋、大有三卦来讲,剥卦是乾宫五世卦,是硕果仅存,不允许这个硕果死亡,让这个剥上九的种子,在果实中发育保存,等到地面上太阳出现的时刻,依据这种环境条件,紧接着决定什么时间生根发芽出土、上升。这样,剥卦成为了晋卦。晋卦之后,就一定是火天大有。就一定会渡过五世时的衰老和游魂卦的心神不定、进退失据的境界。
任何一个纯宫卦,皆有一个经过五世变化后显得衰老的五世,也皆有一个通过五世如游魂一样念念不忘故土、力求恢复故土基业的愿望。在这种愿望的恢复过程中,通过艰难的奋斗,就会进入归魂阶段,亦即在本宫卦里发展得最为辉煌和稳定的状态。
任何一个宫里的八个卦,可能本卦是一个不变本性的卦,是一个最能够预示其本来面目的卦。所谓纯卦、静卦。而其它七卦,都是这个宫、亦即这个时刻段落里生长于特别规定的空间里的生命事物发展变化的七个阶段和状态。假如将之作为一个公式、流程,将出在夏至乾阶段的生命事物定为乾宫,它的命数轨迹就或许是后遁否观剥晋大有。其它各宫里的卦也以此类推。古哲非常可能以此流程和公式来考察生命事物的变化过程,考察人的毕生。
游魂卦的上爻在占疾病或气运时预示什么呢,具体还要看卦辞。一般而讲,不能够命终。
1.晋卦,上六:晋其角,维用伐邑。厉吉,无咎,贞吝。
2.大过卦,上六:过涉灭顶,凶,无咎。
3.明夷卦,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后入于地。
4.中孚卦,上六:翰音登于天,贞凶。
5.需卦,上六爻: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
高岛实际案例:明治二十二年十二月,友人神保长兵卫的老婆因患胃癌而睡床,我占问她的生死,筮得需卦,变为小畜卦。
断卦说:需的卦义是等待,又属于游魂卦。游魂,指人的魂魄已经离开身体而出游,说明天命已绝,只有需缓等待,暂时还不错保有剩余的生命。上爻居全卦的终位,由于无处可去而返回,所以主疾病重而死,魂魄复归本位。爻辞的“入于穴”,是埋葬的预兆,“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指僧人来为她送葬,“敬之终吉”,是指心魂安固。需卦固然不是归魂卦,但是从爻辞可知,她必死无疑。
后来没几天,她果然死了。
6.颐卦,上六:由颐,厉吉,利涉大川。
7.讼卦,上六:或锡之鞶带,终朝三褫之。
8.小过卦,上六:弗遇过之,飞鸟离之,凶,是谓灾眚。
高岛实际案例:某友人来,请占他儿子的病,筮得小过卦,变为旅卦。
断卦说:卦象像飞鸟,上爻为鸟翼。像鸿毛遇见顺风一样,这是飞鸟所心爱的,但是前面的没有遇见,后面的又越过,这便是鸟为啥飞翔不止,属于自取凶咎的做法。此刻您占儿子的病而得到如此的爻辞,上爻处于震动的极位,震又为长子,可知您必然是长子患病。爻象不得中位,可知病一定是过寒的症状,医生不考察他过寒,又施以寒凉的药剂,所以病更凶险了。鸟遭遇罗网是活着被捕捉,还不死。象征他的病还有存活的希望。这一爻业已是卦终,下卦为既济,既济指得以度过险难,这样看来病况又能够挽回了。
六十四卦中,第7师卦、第8比卦、第一3同人卦、第一4大有、第一7随卦、第一8盅卦、第五3渐卦、第五4卦归妹共八个卦,叫做归魂卦,假如占命数得到这几个卦的上爻,就是到了命终的时刻。《系辞传》说:“原始反终,故知死生知说”。即由这几个卦而知道人的命终。人的生死有正命和非命之别。心魂对肉体的依附,就打比方说人的身体寄寓在住宅,心魂脱离肉体,犹如住宅的期限已满 ,心魂离去而身体死亡,称之为正命。期限未满,或许住宅就败坏了,打比方说得病,或遇见其他无比的灾祸,肉体已经死去,心魂突然断绝,称之为非命。要拯救这种非命的死,恐怕良医也无可奈何。三百八十四爻中,得正命而死的只有这八爻罢了。
归魂卦的特征,正好和游魂卦相反,游魂卦为“变”,归魂卦为“不变”。预测推算事物的发展,图谋事情的成功,如逢归魂卦则是心有定向、不变更、不易改变之象,预测推算时,如出现变化后来的事情,也会以主象或原象的不变为主,使出现的新事受到拘泥而不易做成功。预测推算出行逢归魂卦,则会使出行难以启动,或假如硬要出行则不顺,测行人何时归,则人必归,因归魂卦为不变,有一个稳定的居处,逢此卦都会安然无恙。归魂之象,所问之事,拘泥而难行,守旧而难变,变则还有复原之情,我欲出,而归魂不得出。游魂卦是将八纯卦的第5爻,阳变阴,阴变阳而成。例如坤卦的五爻阴变阳成比卦,震卦的五爻阴变阳成随卦,以此类推,反之回推到八纯。
占一自个的气运或健康时,占到这八个归魂卦的八个上爻时,一般而讲,代表命终。要多加注意和提防。
1.大有卦,上六: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高岛实际案例:明治15年,占某贵显气运,筮得大有卦,变为大壮卦。
断卦说,卦象如日中天,五个阳爻所象征的众多贤人辅佐着六五,从中可以看见大有时代的情况。此刻占得上爻,象征行善积德,获得了上天的佑助。这样天下事就没有不吉利的,叫做“天自佑之,吉无不利”。
但这年某贵显死了,由于大有卦的终爻为归魂卦,是人命关天的征兆。
2.随卦,上六:拘系之,乃从维之,王用亨于西山。
高岛实际案例:南部的山本宽次朗是我的旧友,他对俺说:“你的周易百占百中,那么我的命什么时间终结,希望你占一下,让我预先知道”。我说:“这极容易”。筮得随卦,变为无忘卦。
断卦说:随卦以震长男从兑少女,又为归魂卦,此刻占得上爻,您的生命将终结于本年。您的老婆在墓前祭祀之象,正展现在爻辞中。“拘系之”,指系连于您,“维之”,指有子女,“亨于西山”,指把您埋葬在家宅的西面。
山本听了冷笑,似乎不介意,随从他的武士或怀疑或冷笑。后来这年的十月,南部某寄信给我说:“山本昨夜突然中风,半身不遂,于是从本国召唤老婆。他的老婆没到时,请借神奈川的别邸中的一户为寓所。不久他的老婆来迎接,一同回到盛罔,到十二月底就死了。”于是那个时候听了我的占断而暗笑的武士,都为此惊叹。
3.师卦,上六: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
4.渐卦,上六: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吉。
5.比卦,上六:比之无首,凶。
6.盅卦,上六: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7.同人卦,上六:同人于郊,无悔。
8.归妹卦,上六: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六爻断生死秘传口诀详细解读,八字断生死解析
六爻断生死秘传口诀
1.忌神动者,遇生忌之日死。
2.忌神静者,遇忌值之日死。
3.用爻随鬼入墓者死。
4.财动助鬼伤用者死。
5.世应变空者死。
6.财旺用空者死。
7.用动化墓者死。
8.用化月破日绝者死。
9.本宫外卦墓于内卦者死。
10.世坐财墓者死。
11.卦化墓绝者死。(乾兑化艮、坎坤艮化巽、离化乾、震巽化坤)喜用神逢月破者死。
12.忌神长生之日死(土为用亥日死,木用巳日死,火用申日死,水用巳午日死,金用寅日死)。
13.土鬼动者,鬼爻长生之日死。
14.卦六冲者,用爻败死墓绝之日死。
15.用空无气者,元神绝而忌神生之日死。
八字断生死
吉凶好测,生死难断。八字断生死是令预测推算者最头痛之事,也是八字最难断的一项。正所谓由于难,一旦断准却又是最能征服人,又最让预测推算者自豪的事,因此历来学易者都对此孜孜以求,结果又望而怯步。
民间比较高人,八字一出,用脑一算,便知此人是死人八字,令求测者惊叹,这肯定不是一朝一夕之事情,具得有丰富实践经验。有的盲人用《禄倒马斜》诀断生死,准确率在60%—70%,用运精熟可达到更高。但《禄倒马斜》诀对有的同类型适用,有的那种却无能为力。其实也就是说看生死方法许多。本门派有三种断生死原则,准确率很高超过《禄倒马斜》法,并且适用面广,对各种类型的四柱皆有一定灵验度。只要灵活使用,准确率可达80%以上。下面将此法公开于世。
卜卦是咸卦 ,变卦是大过卦,请问怎么解?
泽山咸是谈婚论嫁的最合适的一卦,可惜变出了大过卦。大过就是错,而且是你的错,你的不明了让他失去了耐心与信心。可以试着去表白你的心迹,结果看你的努力了。不过从卦上看可能性较小了。
《朱子语类》卷三十七 论语十九
◎子罕篇下
△法语之言章
"法语之言","巽与之言",巽,谓巽顺。与他说,都是教他做好事,如"有言逊于汝志"。重处在"不改、不绎"。圣人谓如此等人,与他说得也不济事,故曰:"吾末如之何也已!"〔端蒙〕
植说:"此章集注云:'法语,人所敬惮,故必从。然不改,则面从而已。'如汉武帝见汲黯之直,深所敬惮,至帐中可其奏,可谓从矣。然黯论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岂非面从!集注云:'巽言无所乖忤,故必悦。然不绎,又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如孟子论太王好色、好货,齐王岂不悦。若不知绎,则徒知古代人们所谓好色,不知其能使'内无怨女,外无旷夫';徒知古代人们所谓好货,不知其能使'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粮'。"先生因曰:"集注中举杨氏说,亦好。"〔植〕
三军可夺帅章
志若可夺,则如三军之帅被人夺了。做官夺人志。志执得定,故不可夺;执不牢,也被物欲夺去。志真个是不可夺!〔泳〕
衣敝缊袍章
"衣敝缊袍",是里面夹衣,有绵作胎底。〔义刚〕
"衣敝缊袍",也有一等人资质自不爱者。然如此人亦难得。〔泳〕
先生曰:"李闳祖云:'忮,是疾人之有;求,是耻己之无。'吕氏之说亦近此意。然此说又分晓。"〔〈萤,中"虫改田"〉〕
问"子路终身诵之"。曰:"是自有普通人,著破衣服在好衣服中,亦无论者。子路自是不把这般当事。" 〈萤,中"虫改田"〉问:"子路却是能克治。如'愿车马,衣轻裘,和朋友共,敝之而无憾'。"曰:"子路自是恁地人,有好物事,犹要与众人共用了。上蔡论语中说管仲器小处一段,极好。"〔〈萤,中"虫改田"〉〕
问:"'子路终身诵之',此子路所以不及颜渊处。盖此便是'愿车马,衣轻裘,和朋友共,敝之而无憾'底意思。然他将来自诵,便是'无那无伐善、施劳'意思。"曰:"所谓'终身诵之',亦不是他矜伐。只是将这个做好底事,'终身诵之',要常如此,便别无长进矣。"又问吕氏"贫与富交,强者必忮,弱者必求"之语。曰:"世间人见富贵底,不是心里妒嫉他,便羡慕他,只是这般见识尔!"〔僩〕
谢教问:"'子路终身诵之',夫子何以见得终其身也?"曰:"只是以大势恁地。这处好,只不合自担当了,便止於此,便是自画。大凡十分好底事,才自担,便也坏了,所谓'有其善,丧厥善'。"〔淳〕
道怕担了。"何足以臧!"〔可学〕
知者不惑章
"知者不惑。"真见得分晓,故不惑。〔泳〕
道夫问"仁者不忧"。曰:"仁者通体是理,无一点私心。事之来者虽无穷,而此之应者各得其度。所谓'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何忧之有!"〔骧〕
"仁者不忧。"仁者,天下之公。私欲不萌,而天下之公在我,何忧之有!〔泳〕
或问:"'仁者不忧',但不忧,似亦未是仁"。曰:"今人学问百种,只是要'克己复礼'。若能克去私意,日间纯是天理,自无所忧,怎样不是仁。"〔义刚〕
陈仲亨说"仁者不忧",云:"此非仁体,只是说夫子之事。"先生曰:"怎样又生出这一项情节!恁地,则那两句也须恁地添一说,始得。这只是统说。仁者便是不忧。"〔义刚〕
"勇者不惧。"气足以助道义,故不惧。故孟子说:"配义与道,无是,馁也。"今有见得道理分晓而反慑怯者,气不足也。〔泳〕
或问"勇者不惧",举程子"明理可以治惧"之说。曰:"明理固是能勇,然便接那'不惧'未得,盖争一节在,所以圣人曰:'勇者不惧。'"〔焘〕
李闳祖问:"论语所说'勇者不惧'处,作'有主则不惧'。恐'有主'字明'勇'字不出。"曰:"也觉见是如此。多是一时间下字未稳,又且恁地备员去。"因云:"前辈言,解经命字为难。近人解经,亦间有好处,但是下语亲切,说得分晓。若前辈所说,或有不大故分晓处,亦不好。如近来耿氏说易'女子贞不字'。伊川说作'字育'之'字'。耿氏说作'许嫁笄而字'之'字',言'女子贞不字'者,谓其未许嫁也,却与昏媾的意思相通,亦说得有理。"又云:"伊川易亦有不分晓处甚多。如'益之,用凶事',作凶荒之'凶',直指刺史、郡守来讲。在那个时候未见有刺史、郡守,岂可以此说。某谓'益之,用凶事'者,言人臣之益君,是责难於君之时,必以危言鲠论恐动其君而益之,虽以中而行,然必用圭以通其信。若不用圭而通,又非忠以益於君也。"〔卓〕
行夫说"仁者不忧"一章。曰:"'勇者不惧',勇是一个果勇必行之意,说'不惧'也易见。'知者不惑',知是一个分辨不乱之意,说'不惑'也易见。惟是仁怎样会不忧?这须思之。"行夫云:"仁者顺理,故不忧。若只顺这道理做去,自是无忧。"曰:"意思也是这样,更须细思之。"久之,行夫复云云。曰:"毕竟也说得粗。仁者所以无忧者,止缘仁者之心便是一个道理。看是甚么事来,不问大小,改天换地来,自家此心各各是一个道理应副去。不待事来,方始安排,心便是理了。不是方见得道理合如此做,不是方去恁地做。"〔贺孙〕恪录别出。
蔡行夫问"仁者不忧"一章。曰:"知不惑,勇不惧,却易理会。'仁者不忧',须思量仁者怎样会不忧。"蔡云:"莫只是无私否?"方子录云:"或曰:'仁者无私心,故乐天而不忧。'"曰:"固是无私。然所以不忧者,须看得透,方得。"杨至之云:"是人欲净尽,自然乐否?"曰:"此亦只是貌说。"洪庆问:"先生说是怎样?"曰:"仁者心便是理,看有甚事来,便有道理应他,所以不忧。方子录云:"仁者理其实就是心,心其实就是理。有一事来,便有一理以应之,所以无忧。"恪录一作:"仁者心与理一,心纯是这道理。看甚么事来,自有这道理在处置他,自不烦恼。"人所以忧者,只是卒然遇事,未有一个道理应他,便不免有忧。"恪录一作:"今人有这事,却无道理,便处置不来,所以忧。"从周录云:"人故有忧者,只是处未得。"〔恪〕
方毅父问:"'知者不惑',明理便能无私否?"曰:"也有人明理而不能去私欲者。然去私欲,必先明理。无私欲,则不屈於物,故勇。惟圣人自诚而明,可以先言仁,后言知。至於教人,当以知为先。"〔铢〕时举少异。
先生说"知者不惑"章:"惟不惑不忧,便生得这勇来。"〔植〕
问"知者不惑"章。曰:"有仁、知而后有勇,然而仁、知又少勇不得。盖虽曰'仁能守之',只有这勇方能守得到头,方能接得去。若无这勇,则虽有仁、知、少间亦恐会放倒了。所以中庸说'仁、知、勇三者'。勇,本是个没紧要底物事。然仁、知不是勇,则做未到头,半涂而废。"〔焘〕
或问:"'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何以与前面'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次序不同?"曰:"成德以仁为先,进学以知为先,此诚而明,明而诚也。""中庸言三德之序怎样?"曰:"亦为学者言也。"问:"何以勇皆在后?"曰:"末后做工夫不退转,此方是勇。"〔铢〕
或问:"人之所以忧、惑、惧者,只是穷理不尽,故如此。若穷尽天下之理,则何忧何惧之有?因其无所忧,故名之曰仁;因其无所惑,故名之曰知;因其无所惧,故名之曰勇。不知二说孰是?"曰:"仁者随所寓而安,自是不忧;知者所见明,自是不惑;勇者所守定,自是不惧。夫不忧、不惑、不惧,自有一次第。"或曰:"勇於义,是义理之勇。如孟施舍、北宫黝,皆血气之勇。"人杰录云:"或曰:'勇是勇於义,或是武勇之勇?'曰:'大约统言之,如孟施舍北宫黝,皆血气之勇。'"曰:"三者也须穷理克复,方得。只如此说,不济事。"〔去伪〕
问:"'知者不惑',集注:'知以知之,仁以守之,勇以终之。'看此三句,恐知是致知、格物,仁是存养,勇是克治之功。"先生首肯,曰:"是。勇是持守坚固。"问:"中庸'力行近乎仁',又似'勇者不惧'意思。"曰:"交互说,都是。如'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三知都是知;'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三行都是仁;'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三近都是勇。"宙。
可与共学章
"可与共学",有志於此;"可与适道",已看到路脉;"可与立",能有所立;"可与权",遭变事而知其宜,此只是大纲如此说。〔可学〕
问"可与适道"章。曰:"这个只说世人可与共学底,未必便可与适道;可与适道底,未必便可与立;可与立底,未必便可与权。学时,须便教可适道;适道,便更教立去;立,便须教权去。"〔植〕
或问:"'可与立',是如'嫂叔不通问';'可与权',是'嫂溺援之以手'?"曰:"然。"〔焘〕
问:"权,地位怎样?"曰:"大贤已上。"〔可学〕
权,是称量教子细著。〔闳祖〕
问:"权便是义否?"曰:"权是用那义底。"问:"中便是时措之宜否?"曰:"以义权之,而后得中。义似称,权是将这称去称量,中是物得其平处。"〔僩〕
经自经,权自权。但经有不能行处,而至於用权,此权所以合经也,如汤、武事,伊、周事,嫂溺则援事。常如风和日暖,固好;变如迅雷烈风。若无迅雷烈风,则都旱了,不能够为常。〔泳〕
苏宜久问"可与权"。曰:"权与经,不可以说是一件物事。毕竟权自是权,经自是经。但非汉儒所谓权变、权术之说。圣人之权,虽异於经,其权亦是事体到那时,合恁地做,方好。"〔植〕(时举同)
"可与立,未可与权",亦是甚不得已,方说此话。然须是圣人,方可与权。若以颜子之贤,恐也不敢议此。"磨而不磷,涅而不缁。"而今人才磨便磷,才涅便缁,怎样更说权变?所谓"未学行,先学走"也。〔僩〕
先生因说:"'可与立,未可与权',权处是道理上面更有一重道理。如君子小人,君子固当用,小人固当去。然方当小人进用时,猝乍要用君子,也未得。当其深根固蒂时,便要去他,即为所害。这里须斟酌时宜,便知个缓急深浅,始得。"或言:"本朝人才过於汉唐,而治效不及者,缘汉唐不去攻小人,本朝专要去小人,所以如此。"曰:"如此说,所谓'内君子,外小人',古代人们且胡乱恁地说,不知何等议论!永嘉学问专去利害上计较,恐出此。"又曰:"'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正其谊,则利自在;明其道,则功自在。专去计较利害,定未必有利,未必有功。"〔宇〕
叔重问:"程子云:'权者,言称锤的意思也。何物以为权?义是也。然也只是说到义。义以上更难说,在人自看怎样。'此意怎样看?"曰:"此如有人犯一罪,性之刚者以为可诛,性之宽者以为可恕,概之以义,皆未是合宜。此则全在权量之精审,紧接着亲审不差。欲其权量精审,是他平日涵养本原,此心虚明纯一,自然权量精审。伊川常云:'敬以直内,则义以方外;义以为质,则礼以行之。'"〔时举〕
问经、权之别。曰:"经与权,须还他中间位置有个界分。如程先生说,则无界分矣。程先生'权即经'之说,其意盖恐人离了经,然一滚来滚去,则经与权都鹘突没理会了。"又问:"权是称锤也。称衡是经否?"曰:"这个以物譬之,难得亲切。"久之,曰:"称得平,不可增添些子,是经;到得物重衡昂,移退是权,依旧得平,便是合道,故反经亦须合道也。"〔焘〕
问经、权。曰:"权者,乃是到这地头,道理合当恁地做,故虽异於经,而实亦经也。且如冬月便合著绵向火,此是经。忽然一日暖,则亦须使扇,当风坐,此便是权。伊川谓'权只是经',意亦如此。但说'经'字太重,若偏了。汉儒'反经合道'之说,却说得'经、权'两字分晓。但他说权,遂谓反了经,一向流於变诈,则非矣。"〔义刚〕
用之问:"'权也者,反经而合於道',此语亦好。"曰:"若浅说,亦不妨。伊川以为权便是经。某以为反经而合於道,乃因此为经。如征伐视揖逊,放废视臣事,岂得是常事?但终是正也。"〔贺孙〕
或问:"伊川云:'权其实就是经。'汉儒云:'反经合道。'其说怎样?"曰:"伊川所说权,是说这处合恁地做,便是正理,须是晓得他意。汉儒语亦未十分有病,但他意却是横说,一向不合道理,胡做了。"又曰:"'男女授受不亲',是常经合恁地。'嫂溺,援之以手',亦是道理合恁地,但不是每常底道理了。譬如冬月衣裘附火,是常理也。忽然天气做热,便须衣夹挥扇,然便不是每常底常理了。公羊就宋人执祭仲处,说得权又怪异了。"又曰:"经是已定之权,权是未定之经。"〔义刚〕
吴伯英问:"伊川言'权其实就是经',何也?"曰:"某常谓不必如此说。孟子分明说:'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权与经岂容无辨!但是伊川见汉儒只管言反经是权,恐后世无忌惮者皆得借权以自饰,因有此论耳。然经总归是常,权总归是变。"又问:"某欲以'义'字言权,怎样?"曰:"义者,宜也。权固是宜,经独不适宜乎?"〔壮祖〕
问:"经、权不同,而程子云:'权即经也。'"曰:"固是不一样:经是万世常行之道,权是不得已而用之,大约不可用时多。"又曰:"权是时中,不中,则无以为权矣。"〔赐〕
或问:"'反经合道'之说,程先生不取,乃云'不必说权,权其实就是经',怎样?"曰:"某常以为程先生不必如此说,是多说了。经者,道之常也;权者,道之变也。道是个统体,贯乎经与权。如程先生之说,则鹘突了。所谓经,众人与学者都能循之;至於权,则非圣贤不可行也。"〔焘〕
或有书来问经、权。先生曰:"程子固曰:'权即经也。'人须著子细看,此项大段要子细。经是万世常行之道,权是不得已而用之,须是合义也。如汤放桀,武王伐纣,伊尹放太甲,此是权也。若日日时时用之,则成甚世界了!"或云:"权莫是中否?"曰:"是此一时之中。不中,则无以为权矣。然舜禹之后六七百年方有汤;汤之后又六七百年方有武王。权也是难说。故夫子曰:'可与立,未可与权。'到得可与权时节,也是地位太煞高了也。"〔祖道〕
或问经与权的意思。曰:"公羊以'反经合道'为权,伊川以为非。若平看,反经亦未为不是。且如君臣兄弟,是天地之常经,不可易者。汤武之诛桀纣,却是以臣弑君;周公之诛管蔡,却是以弟杀兄,岂不是反经!但时节来这里,道理当恁地做,固然反经,却自合道理。但反经而不合道理,则不可。若合道理,亦何害於经乎!"又曰:"合於权,便是经在其中。"正甫谓:"'权、义举而皇极立',权、义只相似。"曰:"义可以总括得经、权,不可将来对权。义当守经,则守经;义当用权,则用权,所以谓义可以总括得经、权。若可权、义并言,如以两字对一字,当云'经、权举'乃可。伊川曰:'惟义无对。'伊川所谓'权便是经',亦少分别。须是分别经、权自是两物;到得合於权,便自与经无异,如此说乃可。"〔恪〕
问:"'可与立',怎样是立?"曰:"立,是见得那正当底道理分明了,不为事物所迁惑。"又问:"程子谓'权只是经',先生谓:'以孟子援嫂之事例之,则权与经亦当有辨。'莫是经是一定之理,权则是随事以取中;既是中,则与经不异否?"曰:"经,是常行道理。权,则是那常理行不得处,不得已而有所通变底道理。权得其中,固是与经不异,毕竟权则可暂而不可常。如尧舜揖逊,汤武征诛,此是权也,岂可常行乎!臂圣人此意,总归是未许人用'权'字。学者须当先理会这正底道理。且如朝廷之上,辨别君子小人,君子则进之,小人则去之,此便是正当底道理。今人不去理会此,却说小人亦不可尽去,须放他一路,不尔,反能害人。自古固有以此而济事者,但终非可常行之理。若是君子小人往往并进,则岂可也?"〔广〕
亚夫问"可与立,未可与权"。曰:"汉儒谓'反经合道'为权;伊川说'权是经所不及者'。权与经固是两义,然论权而全离乎经,则不是。盖权是不常用底物事。如人之病,热病者当服叙药,冷病者当服热药,此是常理。然有时有热病,却用热药去发他病者;亦有冷病,却用冷药去发他病者,此皆是不可常论者。然须是下得是方可。若有毫釐之差,便至於杀人,不是则剧。然若用得是,便是少他不得,便是合用这个物事。既是合用,此权也,因此为经也。大抵汉儒说权,是离了个经说;伊川说权,便道权只在经里面。且如周公诛管蔡,与唐太宗杀建成元吉,其推刃於同气者虽同,而所以杀之者则异。盖管蔡与商之遗民谋危王室,此是得罪於天下,得罪於宗庙,盖不得不诛之也。若太宗,则分明是争天下。故周公可以谓之权,而太宗不可谓之权。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也。'故在伊尹可以谓之权,而在他人则不可也。权是最难用底物事,故圣人亦罕言之。自非大贤以上,自见得这道理合是恁地,了不得也。"〔时举〕
因论"经、权"二字,曰:"汉儒谓'权者,反经合道',却是权与经全然相反;伊川非之,是矣。然却又曰'其实也就是说未尝反经',权与经又却是一个,略无分别。恐如此又不得。权固不离於经,看'可与立,未可与权',及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事',毫釐之间,亦当有辨。"文蔚曰:"经是常行之理,权是适变处。"曰:"大纲说,固是如此。要就程子说中分别一个异同,须更精微。"文蔚曰:"权只是经之用。且如称衡有很多星两,一定而不可易。权往来称物,使轻重恰好,此便是经之用。"曰:"亦不相似。大纲都是,只争些子。伊川又云:'权是经所不及者。'此说方尽。经只不过是一个大纲,权是那精微曲折处。且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此是经常之道,怎样动得!其间有该不尽处,须是用权。权即细密,非见理大段精审,不能识此。'可与立',便是可与经,却'未可与权',此见经权毫釐之间分别处。庄子曰:'小变而不失其大常。'"或曰:"庄子意思又别。"曰:"他大约亦是如此,但未知他将甚做大常。"〔文蔚〕僩录别出。
经与权之分,诸人说皆不合。曰:"若说权自权,经自经,不相干涉,固不可。若说事须用权,经须权而行,权只是经,则权与经又全无分别。观孔子曰'可与立,未可与权';孟子曰'嫂溺援之以手',则权与经须有异处。虽有异,而权实不离乎经也。这里所争只毫釐,只是诸公心粗,看不子细。伊川说:'权只是经',恐也未尽。尝记龟山云:'权者,经之所不及。'这说却好。盖经者只是存得个大法,正当底道理而已。盖精微曲折处,固非经之所能尽也。所谓权者,於精微曲折处曲尽其宜,以济经之所不及耳。因此讲'中之为贵者权',权者其实就是经之要妙处也。如汉儒说'反经合道',此语亦未甚病。盖事也有那反经底时节,只是不可说事事要反经,又不可说全不反经。如君令臣从,父慈子孝,此经也。若君臣父子都是如此,固好。然事有必不得已处,经所行不得处,也只得反经,依旧不离乎经耳,所以贵乎权也。孔子曰:'可与立,未可与权。'立便是经。'可与立',则能守个经,有所执立矣,却说'未可与权'。以此观之,权乃经之要妙微密处。非见道理之精密、透彻、纯熟者,不足以语权也。"又曰:"庄子曰'小变而不失其大常',便是经权之别。"或曰:"恐庄子意思又别。"曰:"他大约亦是如此,只不知他把甚么做大常。"又云:"事有缓急,理有小大,这样处皆须以权称之。"们问:"'子莫执中。'程子之解经便是权,则权字又似海说。如云'时措之宜',事事都有自然之中,则似事事皆用权。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言之,则'权'字须有别。"曰:"'执中无权',这'权'字稍轻,可以如此说。'嫂溺援之以手'之权,这'权'字却又重,亦有深浅也。"〔僩〕
问:"伊川谓'权只是经',怎样?"曰:"程子说得却不活络。如汉儒之说权,却自晓然。晓得程子说底,得知权也是常理;晓不得他说底,经权却鹘突了。某之说,非是异程子之说,只是须与他分别,经是经,权是权。且如'冬日则饮汤,夏日则饮水',此是经也。有时天之气变,则冬日须著饮水,夏日须著饮汤,此是权也。权是碍著经行不得处,方使用得,然却依前是常理,只是不可数数用。如'舜不告而娶',岂不是怪差事?以孟子观之,那时合如此处。然让人人不告而娶,岂不乱大伦?所以不可常用。"〔赐〕夔孙录详,别出。
问经、权。曰:"'冬日则饮汤,夏日则饮水',此是经也。有时行不得处,冬日须饮水,夏日则饮汤,此是权也。此又依前是经。但经是可常之理,权是碍著经行不得处,方始用权。然当那时却是常理。如"舜不告而娶",是个怪差底事。然以孟子观之,却也是常理。只是不可常用。如人人不告而娶,大伦都乱了!因推说汤武事。伊川说'权却是经',却说得死了,不活。如某说,非是异伊川说,其实就是须为他分别,经是经,权是权。如汉儒反经之说,却经、权晓然在眼前。伊川说,晓得底却知得权也是常理,晓不得底却鹘突了。如大过卦说:'道无不中,无不常。圣人有小饼,无大过。'某谓不须恁地说,圣人既说有大过,直是有此事。但云'大过亦是常理',则得。因举晋州蒲事,云:"某旧不晓文定之意。后以问其孙伯逢。他言此处有意思,但难说出。如左氏分明有称晋君无道之说。厉公信有罪,但废之可也。栾书中行偃直杀之则不是。然毕竟厉公有罪,故难说出。后必有晓此意者。"〔夔孙〕
问:"'可与立,未可与权',看来'权'字亦有两样。伊川以权只是经,盖每日事事物物上称量个轻重处置,此权也,权而不离乎经也。若论尧舜禅逊,汤武放伐,此又是大底权,是所谓'反经合道'者也。"曰:"只一般,但有小大之异耳。如尧舜之禅逊是逊,与人逊一盆水也是逊;汤武放伐是争,争一个弹丸也是争。康节诗所谓'唐虞玉帛烟光紫,汤武干戈草色萋',大小不同而已矣。'尧夫非是爱吟诗',正此意也。伊川说'经、权'字,将经做个大底物事,经却包得那个权,此说本好。只是据圣人说'可与立,未可与权',须是还他是两个字,经自是经,权自是权。若如伊川说,便用废了那'权'字始得。只是虽是权,依旧不离那经,权只是经之变。如冬日须向火,忽然一日大热,须著使扇,这就是反经。今须是晓得孔子说,又晓伊川之说,方得。若相把做一说,如两脚相并,便行不得。须还他是两只脚,虽是两只,依旧是脚。"又曰:"要不是大圣贤用权,少间出入,便易得走作。"〔僩〕
恭父问"可与立,未可与权"。曰:"'可与立'者,能处置得常事;'可与权'者,即能处置得变事。虽是处变事,而所谓处置常事,意思只在'井以辨义,巽以行权'。此说义与权自不同。汉儒有反经之说,只缘将论语下文'偏其反而'误作一章解,故其说相承曼衍。且看集义中诸儒之说,莫不连下文。独是范纯夫不如此说,苏氏亦不如此说,自以'唐棣之华'为下截。程子所说汉儒之误,固是如此。要之,'反经合道'一句,细思之亦通。缘'权'字与'经'字对说。才说权,便是变却那个,须谓之反可也。然虽是反那经,却不悖於道;虽与经不同,而其道一也。因知道伊川之说,断然经自是经,权亦是经,汉儒反经之说不是。此说 不能不知。然细与推考,其言亦无害,此说亦 不能不知。'义'字大,自包得经与权,自在经与权过接处。如事合当如此区处,是常法如此,固是经;若合当如此,亦是义当守其常。事合当如此区处,却变了常法恁地区处,固是权;若合当恁地,亦是义当通其变。文中子云:'权义举而皇极立。'若云'经、权举',则无害。今云'权、义举',则'义'字下不得。何故?却是将义来当权。不知经自是义,权亦是义,'义'字兼经、权而用之。若以义对经,恰似将一个包两物之物,对著包一物之物。"行夫云:"经便是权。"曰:"不是说经便是权。经自是经,权自是权。但是虽反经而能合道,却无背於经。如人两脚相似,左脚自是左脚,右脚自是右脚,行时须一脚先,一脚后,相待而行,方始行得。不可将左脚便唤做右脚,右脚便唤做左脚。系辞既说'井以辨义',又说'井居其所而迁'。井是不可动底物事,水却可随所汲而往。如道之正体却一定於此,而随事制宜,自莫不当。因此讲'井以辨义',又云:'井居其所而迁。'"〔贺孙〕
唐棣之华章
问"唐棣之华,偏其反而"。曰:"此自是一篇诗,与今常棣之诗别。常,音裳。尔雅:'棣,栘,似白杨,江东呼夫栘。常棣,棣,子如樱桃可食。'自是两般物。此逸诗,不知那个时候诗人思个甚底。东坡谓'思贤而得不到之诗',看来未必是思贤。但夫子大约止是取下面两句云:'人但不思,思则何远之有!'初不与上面说权处是一段。'唐棣之华'而下,自是一段。缘汉儒合上文为一章,故误认'偏其反而'为'反经合道',所以错了。晋书於一处引'偏'字作'翩','反'作平声,言其花有翩反飞动之意。今无此诗,不可考据,故不可立为定说。"去伪。
或问"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一章。时举因云:"人心放之甚易,然反之亦甚易。"曰:"反之固易,但恐不能得他久存尔。"〔时举〕
怎样正确对待易经占卜术数
这个浮躁的时代,在这个功利的社会背景下,人们多多少少都带有急功近利的思想。在这样的状况下,指望大家对《易经》那玄奥深厚的哲学理论产生兴趣是不太现实的。谈《易经》哲学容易是阳春白雪曲高和寡,而且《易经》哲学思想太博大精深,从古至今,学者钻石的结果也是见仁见智。另一边,大家对象数派发展衍生出来的数术分支却非常有兴趣。故此我们为啥不加以诱导,从实用预测推算的角度入手作为一个方便法门,引发大家学习传统文化的兴趣,认识到咱们祖宗的文化质朴平实的一面,摒弃那些神神怪怪的糟粕,更客观清醒地对传统文化有个比较全面正确的认识。假如能进而让大家对《易经》产生兴趣去学习研究不是更好吗?当然,数术预测推算在名符其实的易学大家眼中看来,不过是末流,"雕虫小技"而已。
易经占卜术数是建立在我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的基础之上的。在其漫长的传承过程中,历代学习钻石的学者或者说方士受封建思想局限,不可避开的搞出各种神乎其神的言论。打比方说把易经占卜术数和姜子牙、黄石公、东方朔、李淳风、袁天罡、诸葛亮、刘伯温等人扯上关系,甚至把这几个人说成是术数发展的决定性人物。不能否认李淳风、袁天罡、诸葛亮、刘伯温等人在易经占卜术数的发展过程中做出过巨大贡献,但是任何一门学术的发展沿革都是在一代又一代研究者的努力研究基础上完成的,决不是靠一两位能掐会算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奇人决定的。而且像姜子牙、张良、诸葛亮等人辅佐君王运筹帷幄、建功立业,是由于他们全面客观地对形势进行了分析,而作出正确的判断,决不会是掐指一算心血来潮的结果。
易经占卜术数其实也就是说是历代学者,在长期对天象人事观测积累的过程中,在我国古代哲学背景下把地球人事变化进行笼统的归纳后,建造出种种变化发展的模型。通过各种计算方法对最终的发展结果作出预测推算。这种变化发展模型和计算方法虽然有其深邃的论理基础和比较准确的实践效果。但是,到目前为止它也不可能作到百占百验,那么我们需要采取信而不迷的态度去研究与应用它。
另外一方面,自从"打倒孔家店"后,受西方实用主义科学观的作用与影响,我国传统文化受到空前的打击。在某些"学者、怀疑论者、唯物主义者"眼中看来,我国传统文化一无是处。特别是在中国阴阳五行、易经、八卦等学术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中医、占卜风水等学术理论,被这几个自诩为"具有科学的实证精神的学者"斥为无稽之谈。回想二十世纪中医在国际医学界的遭遇,身为中国人,不得不为之扼腕。我曾经就传统术数的论理和许多批判传统学术的所谓学者进行过探讨。他们给我的答案要么顾左右来讲它,要么似是而非东拉西扯的谈一通大道理。其实也就是说,站在客观的立场上看,批判必须以了解作为标准基础。啥都不清楚凭什么去批判呢?人云亦云就是经常提到的"科学的实证精神"?
西方实用主义科学观本身并没有啥不好。我国传统文化里也有许多糟粕。但是,我们不能由于此刻世界学术界是的西边方学术思想为主流,就不分青红皂白大肆批驳咱们祖宗传承了数千年的灿烂的文化结晶。谈来这里我想讲一点题外话。前不久得知网上有人在网上发帖大谈要求中医5年内退出国家医疗体制,企图取消中医的言论。能够想象,在不久的将来将会有人"语不惊人死不休"地提出要全面取消易经以及其派生的诸多学术了。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学术,我们的历史就是毁在这几个数典忘祖的败家子手里了。
鉴于当前"百家争鸣"而又是西方学术思想占主导和霸权地位的形势,我觉得对待易经占卜术数的态度应该是,既不盲目迷信也不妄加否定,不参与无谓的讨论,应以客观的立场埋头钻研与实践,亲身体验和检验它,发展完善它。终究,身为华夏儿女的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将俺们伟大灿烂的文明传承发展下去。